李凯航评《思想地震》|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与“终结”
- 炒股技巧
- 2025-04-12 11:15:05
- 7

《思想地震:柄谷行人演讲集:1995-2015》,[日]柄谷行人著,吉琛佳译,上海文艺出版社,2024年7月出版,252页,58.00元
一
1970年代,柄谷行人曾专注于文学史中的“起源”问题(见《现代日本文学的起源》)。但他又强调,“起源”不可追溯得太远,因为这种“谱系学的溯源”方式暗藏着陷阱。例如,许多现代日本民族主义者跑到本居宣长那里寻找日本文学的特殊性,或者像德里达在古希腊中寻找“声音中心主义”,实际上是对起源的忘却。与之相反,汉娜・阿伦特从十九世纪后期国民经济的确立过程中考察反犹主义的起源,就保持了一个适当的距离。因为“现代反犹主义是在传统的民族主义衰朽时生长起来的,并且恰恰在欧洲的民族国家制度及其权力失衡被摧毁时达到了顶峰”(见《极权主义的起源》)。柄谷对现代日本的文学“起源”的追溯,聚焦在了日本民族国家形成期的明治二十年代(1887—1897)。他认为,那是一种通过一系列表现手法,例如“风景”、“内面”、“儿童”之“发现”、“言文一致”等等建构起来的“民族国家”(national state)意识形态。

柄谷行人
然而到了1990年代,这种“文学”终结了。此后年轻人追求的是“现代思想”,而不是“文学”。柄谷批判道,“现代文学已经丧失了其破坏性的否定力量,成了国家钦定教科书中选定的教材,这无疑已是文学的僵尸了”。也就是在这个时期,他放弃了“文学”,转向了“心理”(《日本精神分析》,2002)、“历史”(《世界史的构造》,2010)、“哲学”(《哲学的起源》,2012)等领域。新著《思想地震:柄谷行人演讲集1995-2015》大致从以上几个方面回顾了这种转折。不过,要理解柄谷为何“放弃”文学之前,需要说明他为何“选择”了文学。柄谷如是说,
我在1960年代初期选择走上文学批评的道路。我当时觉得如果做了文学批评,那就无论什么都可以做了。……战后的日本存在一种对文学批评不同寻常的信任。这是因为哲学和社会科学在战前和战时曾经丑态毕露到了致命的地步。到战后,只有文学批评还得以残存下来。文学并没有舍弃感性的个人维度,且又能够同时捕捉到超越个人的社会结构等维度。换句话说,文学批评使我们得以在把握这个世界的同时,不至于舍弃了自身的存在。(引文若未注明来源,皆出自《思想地震》)
从战前开始,“文学批评在日本便作为一种与哲学和社会科学相抗衡的知识形式而存在”。关于这一点,只需要去看竹内好所代表的“中国文学研究会”是如何抵制旧的“支那学”就一目了然了。“文学”在他那里也是一种方法(见孙歌:《竹内好的悖论》)。这个时代的“文学”,正如萨特所言,“一言以蔽之,就是一个处于不断革命中的社会的主体性”。
当然,“文学”并非一直处在这种优越的地位上。柄谷指出,这其实是十八世纪的康德提倡美学(aesthetics),“理性”与“感性”的关系“颠倒”以后的事情。“到那时为止的哲学里,感性、情感一直被看成是比较次等的人类能力。人们更希望的是能够排除感性,达到理性的境界。然而用新的态度来看,感性、情感与认知和道德能力(知性和理性)紧密联系,双方经由想象力的中介作用而相互关联。想象力以前一直被看成负面的东西,因为它会给人造成幻觉。但从这时起,想象力被奉为创造性力量,开始得到称颂。这一情况与文学的受人重视之间有着密切关联。”其实,民族也只能存在于这种“想象力”之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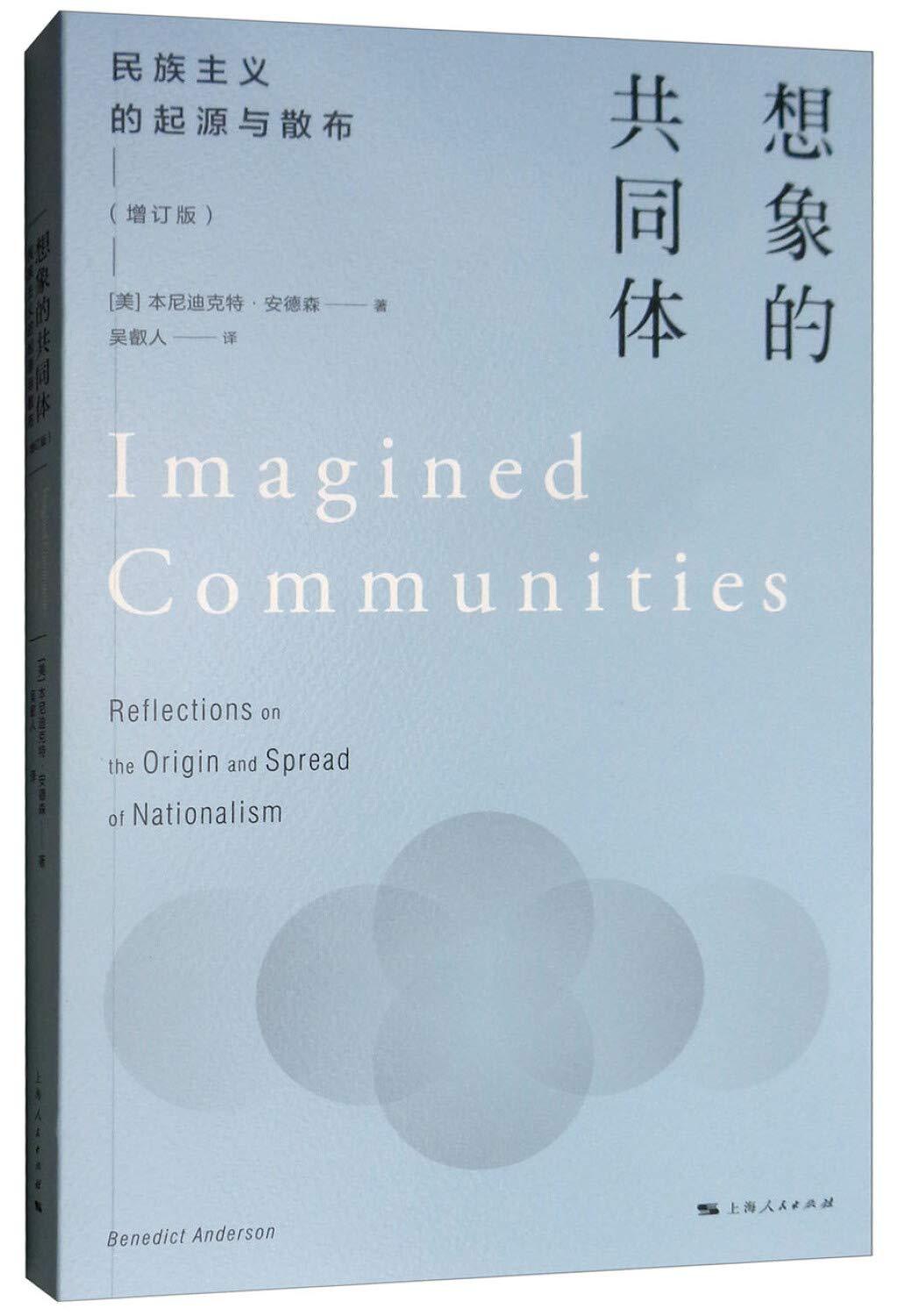
《想象的共同体》
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重视报纸这种印刷资本主义的代表不同(见《想象的共同体》),柄谷特别强调小说这种新的文学形式在民族形成中的作用。“对于一个民族——作为‘共情’的共同体,也即想象的共同体——的建构而言,小说成了基础。小说让知识分子与大众,也即让不同的社会阶层,都能借助这一‘共情’而变得一样,从而形成了民族共同体。”“以德国为例,在十九世纪下半叶普鲁士统一全国之前,德国人分为许多小国,也分为许多相互之间争斗不止的宗教派系。这期间,能够让他们作为一个民族统一起来的只有文学。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德意志民族不是别的,就是德国文学。”
另一方面,柄谷对“nation”被翻译成“民族”持有异议。“民族(ethnic)是亲族和族群的延长,乃建立在血缘和地缘上之共同体。所谓nation应该理解为由脱离了此种血缘地缘性共同体的诸个人(市民)而构成的。”多族群构成的美国的“nationalism”十分强烈,但那不是“民族主义”,因为它“强调合众国是由每个个人构成的nation,即以自由为存在的根据”。“Nation是因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扩张族群共同体遭到解体后,人们通过想像来恢复这种失掉的相互扶助之相互性(reciprocity)而产生的。”“同时,nation也非仅以市民之社会契约这一理性的侧面为唯一的构成根据,它还必须根植于如亲族和族群那样的共同体所具有的相互扶助之同情心(sympathy)。”

康德与斯密
这就是为何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撰写《道德情操论》并提倡“同情”的原因。“同情”看起来与“宗教里说的怜悯或者慈悲类似,实则不同”。斯密所说的“同情”,指的是“站在他人立场思考的‘想象力’,这毋宁说是对利己主义的肯定,也是现代市场经济成立的前提。因此,同情是在前现代的共同体遭到瓦解、利己主义渗透之后出现的事物”。“同情”在这种语境中是一种全新的情感。“在同情中,感情有了与以往不同的价值。在十八世纪的英国文学中,感伤主义(sentimentalism)一词作为一种新的态度,被人们以正面的意义使用了。”
二
在新著中,柄谷还补充了一个此前被忽视的视角,即“内在之人的产生源于政治上的挫折”。具体说来,是北村透谷在明治一〇年代的自由民权运动失败后,转向了以“想世界”对抗“实世界”的文学活动,因而具有了某种“内在性”。一般的研究也将此视为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但柄谷认为,透谷并不是在逃避政治现实,在甲午战争中他反而继续积极地介入了反战运动。后来,现代日本的文学也并未按照透谷的方法发展起来。同一时期坪内逍遥提出的“现实主义”(即自然主义),毋宁说是对他这种“想世界”的讽刺。因为那是一种反对一切理想的“写实主义”,不论这种“理想”是儒教的“劝善惩恶”,还是西洋的“自由民权”。当然,如果帝国主义是基于优胜劣汰的科学法则,实现了“理想的秩序”的话,逍遥也会反对。然而,如果帝国主义的弱肉强食是一种“现实”,则另当别论了。就这样,与法国或德国的现实主义支持社会主义相反,日本的现实主义间接地支持了帝国主义。在柄谷看来,代表这种趋势的不是透谷,而是国木田独步。

北村透谷与国木田独步
在《难忘的人》(1898)一文中,独步通过“颠倒”背景与风景的关系,写出了“内在之人”的苦闷。“其时油然浮上心来的即是这些人,不,是站在看到这些人时的周围光景中的人们。我与他人有何不同,不都是在天之一角得其此生而匆匆行路,携手共归无穷天国的人吗?当这样的感想由心里升起时我便常常泪流满面。那时,实际上乃是无我无他的,什么人都变得令人怀念起来。”
在独步看来,“难忘之人”并不是“不能忘掉的人物”,毋宁说是“那些没有意义、无足轻重”,即“作为一种风景的人”。这种“颠倒”在其他领域内同时发生,例如在绘画中,纯粹的风景取代了欧洲的宗教画或中国的山水画中的形而上学或写意的主题;在语言学中,“声音”取代“文字”,形成了所谓的“言文一致”;在民俗学中,柳田国男也摒弃了儒教的“经世济民”中的“平民”或“农民”,发现了民族的载体“常民”等等(见子安宣邦:《一国民俗学的确立》)。
正如石川啄木在《时代闭塞之现状》(1910)中指出的一样,这样的自然主义看似与国家对立,其实不然,“日本的年轻人从未与国家的权力做过任何斗争”,“因此,国家成为我们之怨敌的情况也还从来没有过”,“我们必须舍弃自然主义,……把我们所有的精力投入到对明天的思考”。事实上,现代日本的自然主义,毋宁说是与日本帝国主义同步成长起来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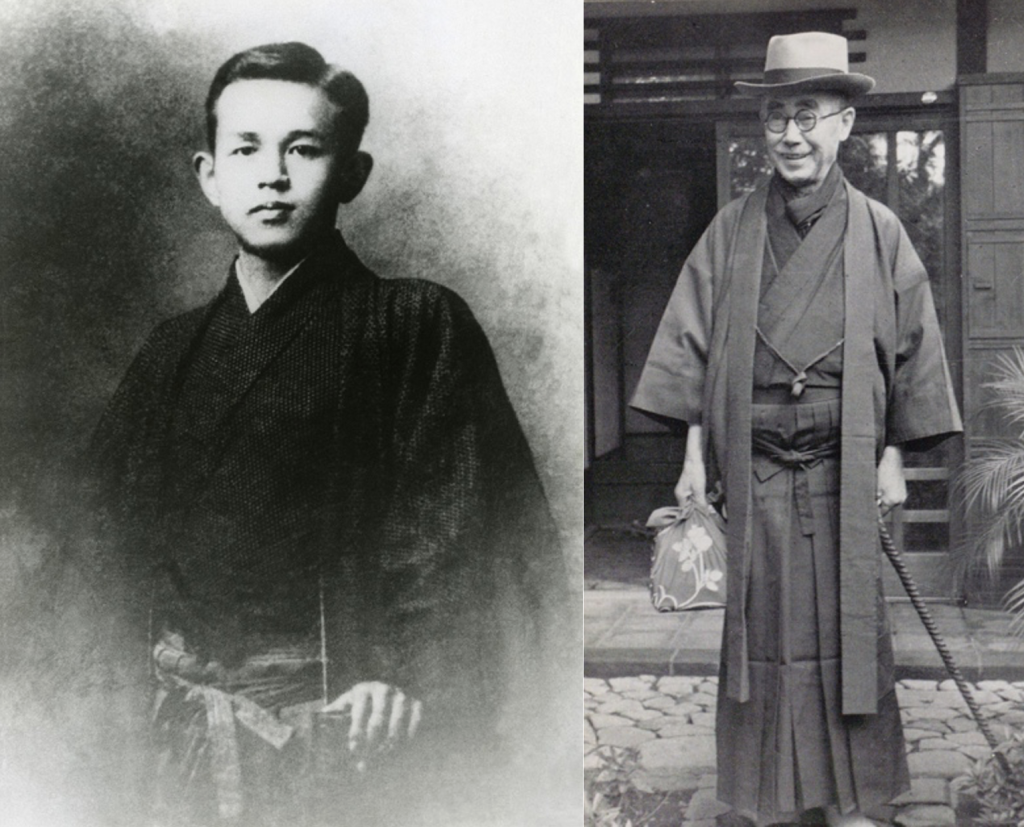
石川啄木与柳田国男
众所周知,甲午战争期间,独步曾担任随军记者,在民族主义浪潮中大受欢迎。战争结束后,他陷入无所事事的迷茫状态,随后移住北海道。他在那里也发现了“风景”。他质问道,“社会在何方?人类傲然传颂的历史,在何方?”不过,这其实是一种“欺骗”。他所去的地方,其实是阿伊努人历史上的定居地。北海道开拓不仅仅是“拓荒”,还是通过杀害和同化阿伊努人实现的。然而,正是通过忽视这些不该被遗忘的重要之事,难忘的风景才得以被“发现”。可以说,日本现代文学与殖民主义有着极为密切的关联。只有对外战争胜利后,日本帝国的压力才可能从外在的世界转向了人们的内心,自然主义者们才能拥有了这样的“自我意识”。而对这样的帝国主义,独步采取的是一种既不迎合,也不反抗的态度。用柄谷的话来说,“他只是一位敏感、内向、写作讽刺内容的作家罢了”。
三
明治二十年代,即十九世纪末期,是近代世界史进入了帝国主义全盛期之时。从殖民主义进程来看,1882年英国在埃及确立了统治地位,1883年法国占领了越南,1884至1885年的柏林会议瓜分了非洲,同年在越南爆发了清法战争,1885年俄罗斯占领了阿富汗,1886年英国又占领了缅甸,同年德国占领了马歇尔群岛,1887年法属印尼联邦共和国成立。帝国主义可谓甚嚣尘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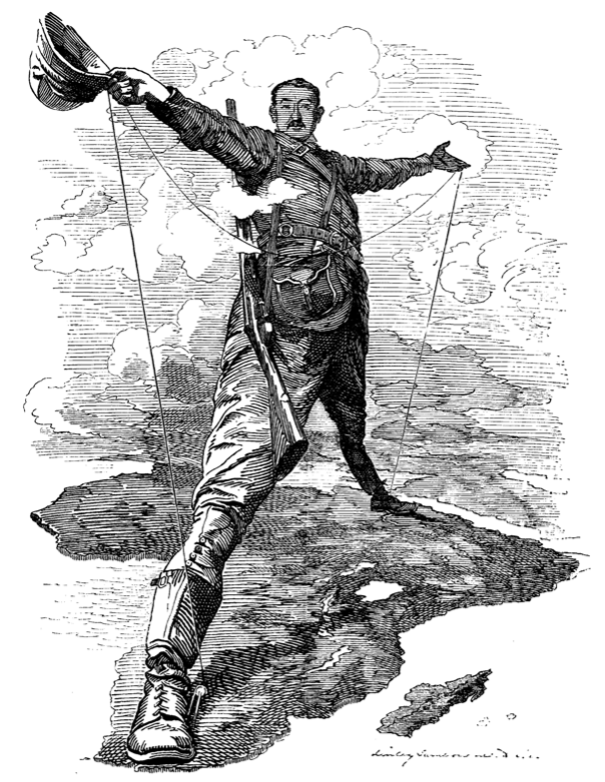
欧洲帝国主义者的宣传画
但是,柄谷并不认“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之解释,而是按照沃勒斯坦的方法,将“帝国主义”和“自由主义”看成是反复上演的循环结构。“自由主义是霸权国家采取的政策,而所谓帝国主义是旧的霸权国家已经衰落,而新的霸权国家尚未确立的时代。”沃勒斯坦认为,历史上只有三个霸权国家,荷兰、英国、美国。他们首先是在制造业上取得绝对的霸权,推广自由主义,然后在制造业优势丧失后依靠商业和金融维持霸权,进入帝国主义阶段。这个过程大约持续六十年。换言之,世界历史每隔一百二十年就会“反复”一次。
如果按照这种解释,美国的帝国主义起源于1930年代,终结于1990年代。在柄谷看来,后冷战时期所谓的“新自由主义”,其实才是真正的“帝国主义”——制造业被迁移出美国,国家从社会福利行业撤退,通过削减发达国家熟练工人的工资,使其适应与发展中国家低成本劳动力的竞争,其权力源头不再是占有领土或剥削资源,而是市场和消费者的组织化,且主要利益由金融等投资中的垄断行业所掌控(见大卫·哈维:《新自由主义简史》)。换言之,1990年后,美国并未进入鼎盛期,反而陷入了衰落之中。

沃勒斯坦
另一方面,从“反复”的视角来看,明治二十年代也是大英帝国呈现颓势,从而进入全球帝国主义的时期。此前英国奉行“自由主义”之时,各种社会政策得到实施,工会势力强大,合作运动繁荣,甚至还有“劳工贵族”的说法。但后来,社会福利被削减,贫富差距扩大。大家开始信奉弱肉强食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明治初期,福泽谕吉所推崇的“独立”“自尊”的英国,是自由主义时代的英国。然而,明治二十年代后,德富苏峰看到的“社会帝国主义”的英国,则是一个全球霸权竞争中日趋衰落的大英帝国(见宇野田尚哉:《成立期帝国日本の政治思想》)。
在日本,帝国主义意识形态也逐渐地取代了自由主义。中江兆民准确地捕捉到了这种转向,“今之欧美诸强所在,帝国主义渐趋兴盛,值此之际,若仍持民权理论,则不通于世界之风潮,而落后于流行也”。“民权”这种个人的“自由主义”已经让位于“国权”这种集体的“帝国主义”了(见松本三之介:《国权与民权的变奏》)。
宫崎学曾发现,以1989年日本经济泡沫破灭为界,市场上先后流行“自我开发”与“自我启发”的书籍。前者虽然也宣扬改造自我,但那是一种为了集体的扩张而进行的自我完善;而后者则是劝导人们以自我为中心进行积极的思考,考取资格证书和提升技能等等。他认为,“自我开发”是泡沫时代,而“自我启发”则是与后泡沫时代的意识形态(《“自己啓発病”社会》)。

宫崎学与村上春树
其实,如果比较明治第一和第二个十年前后,就会发现也有类似的转变。1871年,中村正直以“西国立志编”为题翻译出版了英国“成功学”鼻祖斯迈尔斯的《自己拯救自己》(Self-Help,1859),畅销一时。斯迈尔斯是工人运动、合作社运动的支持者。在大英帝国“自由主义”时期生活的他宣扬的自助,与互助精神密不可分,自助意味着工人应当相互帮助,而不是依赖国家。但明治中后期的日本人却将此曲解为,要是不能自我拯救就只能被吞并的社会达尔文主义。面对这种现实,如前所示,国木田独步选择视而不见。正如他在北海道看到的只是“风景”,而不是“阿依努人”一样。
那么,后冷战时期如何呢?如同独步将“微不足道但令人难忘的事情”作为“风景”加以强调一样,村上春树在《1973年的子弹球》(1980)中也进行了类似的“颠倒”。众所周知,《1973年的子弹球》的题目借用了大江健三郎的《万延元年的足球队》(1960)。1960年是安保斗争之年,大江往上回溯百年,描绘了一个通过足球队武装起来反对核武、军事占领,映射日美畸形关系的寓言故事。对此,村上戏谑地仿写道,“1960年,是鲍比・维演唱Rubber Ball的那一年”,“1969年,当时我二十岁”,“那时我迷恋着女孩子呢”等等。正是通过这样的“颠倒”,“安保斗争”“全共斗”(1969年)等政治现实被解构掉了。柄谷认为,如果战后的大江健三郎是明治的北村透谷,那么村上春树就是国木田独步。这是现代日本文学发展的两种不同方向。如今,村上成为了当代日本文学的主流。为何现代日本文学会以这样的方式发展呢?柄谷认为这与近代日本缺乏“中间势力”有关。
四
1920年代,和辻哲郎在德国留学时曾发现,在德国共产党示威时,其支持者会在窗口挂上红旗以示声援,而反对者则挂上了帝国旗。这个时期,无论是纳粹还是共产党其实都是少数派,但在他们的活动中,几乎每家每户都鲜明地表达了态度。和辻认为,日本的无产阶级运动则不是这样,基本上是“领导者”的运动,与普通日本人的关系不大。深谙狄尔泰文化史学的和辻写道,在西方,人们被纳入城市共同体,通过城墙与外界隔开。而在日本,个人存在于篱笆所围成的家族之中。“城墙内部,人们团结一致共同对敌,联合一切力量保卫自己的生命”,“共同事业成为生活基调,规定了所有的生活方式”,“义务意识在一切道德意识的最前面”,而日本人只是关心如何把“家族”内部搞的丰富多彩。于是,“城墙”与“锁”成为了西方与日本两种生活方式的象征(《风土》)。

全共斗运动
战后,丸山真男试图解释为何消极的日本人集体性地参与了狂热的法西斯运动。不同于和辻的文化史学解释,他强调“中间势力”在塑造政治运动中的重要性。在《个体析出的种种模式》(1968)中,他将脱离传统共同体的人分为四种类型:“民主化”(democratization)、“自立化”(individualization)、“原子化”(atomization)、“私人化”(privatization)。“民主化”与“自立化”都是具有联合性的个人,只不过“民主化”强调中央集权的方式,而“自立化”更强调地方自治。“私人化”与“原子化”属于非联合性的个人。“私人化”是“民主化”的反面,拒绝一切政治活动,只关心自己私人的事物。用和辻的话来说,他们属于活在“篱笆所围成的家族”里的人。而“原子化”相对“私人化”而言,“缺乏属于私人的内核,是一些一味追随大众社会、随波逐流的个体”。“原子化的个人一般对公共问题不甚关心,但正是这种不关心往往会突然转化为狂热的政治参与,也就是说他们为摆脱孤独和不安而焦虑。正因为如此,这种人才会全面归依权威主义的领导,或是忘我地投入到那种民族共同体、人种特质永存观念所表现出的神秘‘集体’中去。”法西斯运动中的狂热分子,正是这种类型的人。他们在“过度政治化和全然的漠不关心”之间来回摆荡。
丸山指出,如果一个社会的近代化是自发形成、渐进展开的,那么“自立化”和“私人化”类型的人便会占较大比例;相反,在后发国家的近代化过程中,更多的是“民主化”和“原子化”类型的人。明治维新后日本的集权化,和昭和日本的“超国家”,正是在“民主化”和“原子化”结合及其极端化过程中形成的。
柄谷指出,如果按照丸山的范式解释现代文学的形成,就不足为奇了。西方的现代小说是基于“自立化”而成立的,而日本并不存在那样的基础,所以只能以“私人化”的类型出现,其在文学上的表现形式就是“私小说”。正如小林秀雄指出的一样,“采取私小说形式的日本自然主义文学,不是资本主义,而是封建主义的文学。日本的自然主义作家,并未意识到个人与社会的对立,‘私’的世界即是社会本来的姿态”。与之相对,“欧洲近代的文学史,对抗着各个时代的统治思想,留下了通过自身肉体表现那个时代痛苦的战斗痕迹。他们的文学一刻都未曾离开过社会与社会思想”。在小林看来,在日本,只有昭和时期输入的马克思主义文学彻底地拒绝了这种私人化的倾向。在那之后,“作家对于日常生活的反抗首次成了至关重要之事。输入的东西并非文学的表现手法,而是社会思想”(《私小说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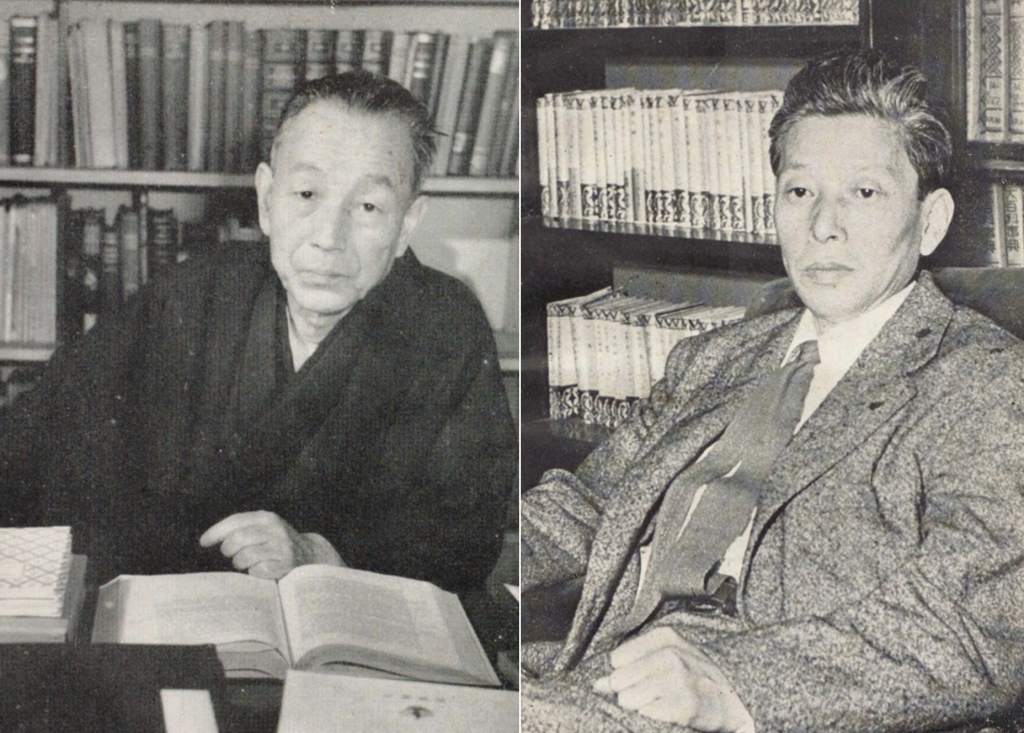
和辻哲郎与小林秀雄
换言之,马克思主义文学试图将日本的“私人化”转换为“民主化”。但它不久就被法西斯主义镇压了下去,被迫转向了。这个时候,大多数人没有转向“自立化”,而是转向了“私人化”与“原子化”。战败后,“民主化”获得了新的契机,共产党又取得了支配性的地位。它不仅否定“私人化”,还要否定“自立化”。但它遭到了“自立化”的抵制,并在1960年代因苏共二十大危机与日共的“六全协”而丧失了权威。与此同时,“自立化”又迅速地在向“私人化”与“原子化”转化。这就是1970年代后的大众消费时代的社会结构。柄谷说道,这并不是日本某个时期的特殊现象,而是现代日本自成立之初,就是建立在摧毁“中间势力”的基础上的。这一过程一直延续到了1990年代。在小泉首相推行的新自由主义的打击下,工会(国劳和日教组)、创价学会、部落解放同盟、朝鲜总联、大学(教授会)自治等等一个个“中间势力”都在日趋没落。现代日本文学的“终结”,也只是其一种表现形式罢了。
(本文为东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基地培育项目“近代日本研究”阶段性成果。)
下一篇:股票持有时间策略探讨










有话要说...